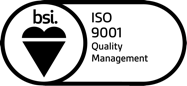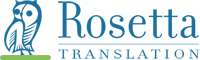自童年起,我就对语言的生命、死亡和维护感到惊奇不已。最近谈到语言的绝迹,我仔细查阅了语言的生命周期,想知道世界上这么多语言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语言的生命
自从我开始为翻译公司写作,我又重燃童年时期对语言的兴趣。
在着手写作前,我已从业10多年的营销传播。正值品牌营销巨头开始从单一国家营销转向区域营销时,我进入了该行业。
他们测试各类营销传播模式(现在仍旧是),想设法找到一种适用于整个市场的工作理念。
为电视提供我们制作的副标题曾风靡一时。我们不得不把稿子翻译成几种语言,我们经常把这样的稿子发往当地周边的几个办公室来完成翻译。
正值那时,我开始对不同种族不同的表达方式益发感到好奇。由于我们的工作涉及品牌个性,有时候在一个国家,有些概念可以用一个词来阐述,但在其他国家,却完全无法做到。
要将稿件中各国表达的情感意图始终如一地翻译出来,这难倒了我。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来确保稿件之间能表达出相同的情感—我们也努力使它们在相同的电视节目播出时间,比如说30秒内出现。有时,我们不得不勉强做“好的/照办”此类的翻译稿,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重新翻译。试想,这是我们在很多国家遇到的一个问题,那里的语言活得不错,而且有数百万的人说着当地的语言。
由于缺乏商业用途,广告被翻译成稀有语种的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这使我很好奇在其它哪些领域内语言生命会显得尤为重要。像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中有很多小派文化,它们依靠口头传述而成为了主要的信息源。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可能丧失了很多柬埔寨的艺术和文化知识,更不要说学习更多柬埔寨的生物多样性了。
我感到世界对柬埔寨的了解陷入了某个时期—杀戮时期。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只把它当作一种记忆,用来暗示永远都不会再发生的东西。
语言的生命和死亡
当我刚与翻译行业接触时,我开始遇到了这样的案例研究。例如,高棉语翻译成英语的项目是极其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说高棉语的人已经消失,更是因为既能说高棉语又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人也已经消失了。柬埔寨仍旧是不对世界开放的国家,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也很难找到一些领域的专家像考古学家或甚至是拥有技术语言技能的工程师来翻译这些项目。另外一个例子是普什图语与达里语的翻译(阿富汗的2种主要语言)。
在政治领域,需要为战乱地区或者甚至仅仅为政治避难苦思构想政治协议,此时要与这些与外界隔离地区的语言打交道,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
除了政府政策和经济隔离地区的问题,连最后一些说稀有语种的人也最终消失时,它们将如何存活?我对此感到好奇。
比如,在秘鲁地区,Chamicuro语言曾被普遍地当成母语来讲。不过,由于不断地使用西班牙语并将之作为主要语言,现在只有年长的那一部分人说Chamicuro语了。 现在孩子只说西班牙语,像诸如Chamicuro语已被列为濒临绝迹的语言了。
最极端的例子就像Kaixana语言(先前由遥远的巴西部落人民所说)或Taushiro语言(也属于遥远的秘鲁部落),它们都被列为只有一个人会说的语言,因而现在,是注定要取得最终的灭亡。
这两种语言的死亡不同于Chamicuro语言,后者是由被更多人所说的另外一种语言所代替。这两种语言是注定要绝迹的,因为使用它们的部落几乎绝迹。
语言,最终与讲该语言人的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活生生的生命。它的日常使用对于它的生长和生命来说至关重要,就像水与食物对我们人类是极其重要的那样。
通婚、移民、政治动荡和政府政策的变革—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语言的生命周期。但是,人类干预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这些因素。只要人们愿意说一种语言,那么它就会活下来。不过,当说一种语言的人们消失殆尽时,人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民族或者是他们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传说、民俗和口头文学传统—我们人类丰富历史的一部分—也损失了。
一方面,我们可以仅仅将这些文化特征的损失视为生命与进化的一部分。部落及其语言的消亡就好比动物的绝迹,我们从未见过它们,而它们曾分布世界各地,那里人类无法涉足,或者已被铲平建造公寓。如果那是语言死亡的唯一理由,那么这要比一些情况,例如,Chamicuro语言的绝迹是因为被另外一种更加商业化的语言所代替,更容易让人信服了。
让语言存活
作为菲律宾移民,这个例子与我更加息息相关,并且更能引起我的共鸣。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千百万的菲律宾人离开了菲律宾,寻求经济上的发迹。
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大民族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定居。在当今这个时代,交通费用廉价、各个领域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大家不断寻求经济机遇,我认为移民入境后会看到更多的人涌入其它国度。
我想我开始担忧我们自己的语言了,因为很少有菲律宾人移民进入他国并且在那成立家庭后,会教他们孩子自己的语言。此外,另一个事实是,建立在塔加拉语基础上的民族语言正在被马尼拉以外其它省份更多的人所讲。
我的一个朋友来自于北方,那里距马尼拉有3个小时的车程, 她告诉我现在讲塔加拉语的人要比讲伊洛卡诺语的人多,而后者是北部主要的语言。
基于塔加拉族语的菲律宾语是近期的一种语言现象。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甚至是到了80年代,很多省份仍旧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尤其是维萨亚斯群岛的人,他们长时间抵制讲塔加拉族语。15年后至今,全国上下都在讲塔加拉族语。
如果你了解我,你也许会说我对菲律宾语言的健康担忧是很奇怪的。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短短的2年,其它时间我并没有住在自己的国家。我的家庭来自于北方,我开始学会讲英语(菲律宾北方讲的是伊洛卡诺语言,与塔加拉族语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在我进入小学前才学塔加拉族语。直到我和我的兄弟最后长大,期间在家里对着我们的长辈说塔加拉族语,我们家才说了塔加拉族语。
奇怪的是,我未尝试过用菲律宾语写作,因为我对该语言的使用技能缺乏自信。还有令人奇怪的是,我对身为伊洛卡诺人感到深感自豪,但我却几乎不能讲我们北方的语言。写下这些时,我感到很滑稽,不过,我离开我的国家越久,我就更加学会了欣赏我们语言的浪漫、抒情和动人。似乎真正是,当你失去后,才开始欣赏曾经拥有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羡慕一位同瑞士绅士结婚的表亲。他们定居在瑞士,育有两子,一个是2岁,另一个是4岁。我的表亲坚决要让她的孩子们说一口流利的菲律宾语、法语和英语。她的菲律宾互裨受到过严格的指示,她们俩只对孩子们说菲律宾语。因而,即使他们每年只回国一次,但她的孩子们能够像在菲律宾长的其他孩子一样,说着一口流利的菲律宾语。
我想正如生活中很多事情那样,这取决于个人的意愿。无论你住在哪或者你无论同谁结婚,语言可以继续存活。任何事物,无论是记忆、梦想或者是语言都能存活—如果你愿意的话。